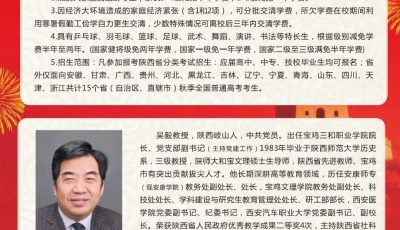在甘泉县的大街小巷常能看到一个步履匆匆的身影。藏蓝色警服的肩章被汗水浸得发亮,皮鞋沾满灰尘,却总在群众招手时立刻放缓脚步——他就是郭江浪,甘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的一名民警,也是从“铁拳师”走出来的兵。

钢枪换警徽 初心磨不掉
2010年寒冬,成都军区某部“铁拳师”的训练场上,郭江浪最后一次擦拭着陪伴他两年的钢枪。枪身的凉意透过指缝传来,像极了他此刻的心情,脱下军装时,那声“到”字哽在喉咙,却在转身时挺得笔直。四年后,当藏蓝色警服穿在身上,他对着镜子敬了个军礼,镜中人眼神里的光,和当年在军营里一模一样。
“保家卫国和为民服务,都是扛着担子往前走。”郭江浪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2020年甘泉县公安局“百警连万家”活动启动时,他包抓的村子在二十公里外的山坳里。第一次去走访,警车在碎石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,他却像在军营拉练时那样,下车就帮路边犁地的老汉扶犁。

老宋家的矛盾,是他啃下的第一块“硬骨头”。老宋的儿子和弟弟因宅基地边界积怨多年,见面就红脖子。郭江浪先去地头帮老宋摘了半筐苹果,听他叹着气说“都是亲人,咋就成了仇人”;又去老宋弟弟家,帮着修好了吱呀作响的木门;晚上蹲在老宋儿子家的灶台前,听他讲在外打工受的委屈。第十三天晚上,他把两家人叫到一起,没讲大道理,只说:“我在部队时,战友的后背能托付生命。现在咱们一个村住着,都是亲戚,低头不见抬头见,哪有解不开的结?”那天的月光洒在院子里,两双手终于握到了一起。
病躯撑硬骨 责任放不下
2022年秋天的重大警卫任务,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。接到命令时,郭江浪正在医院拿体检报告,医生在单子上圈出“急性胃溃疡加重,需静养”的字样,被他随手塞进了裤兜。
那三十天,他的脚步像装了发条。白天在现场反复排查路线,皮鞋底磨出了洞;晚上在办公室核对方案,台灯亮到凌晨。同事见他脸色发白,递过保温杯,他笑着说“没事”,转身却蹲在走廊里,按住绞痛的胃大口喘气。有天凌晨两点,他突然直不起腰,额头抵着墙面缓了十分钟,又扶着墙回到办公桌前——桌上的任务清单还有三分之一没细化。
任务结束那天,他值完勤后蜷缩在警车后座上靠着车门就睡着了。同事拍的照片里,他头发乱糟糟地粘在额头上,胡茬泛着青黑,嘴角却微微上扬。后来大家才知道,那阵子他的通话记录里,每天只有三个电话,早晨六点给指挥部报平安,中午十二点报进度,凌晨一点跟妻子说句“别等我”。妻子心疼他,要来看望,他总说“忙完这阵就好”,可这阵忙完,下一阵又接上了。
铁汉有柔肠 民心暖得透
在派出所工作时,郭江浪的警服口袋里,总装着两样东西:创可贴和民情本。创可贴磨破脚时用,民情本记着谁家的孩子该上户口,谁家的低保还没落实。有次在山梁上遇见放羊的老汉摔了跤,他背着老人走了三里地,汗水把警服浸透成深蓝色,老人在他背上念叨:“这娃娃,比我亲儿子还实在。”
从军营到警营,十二年过去,他手臂上的伤疤淡了,可“铁拳精神”像刻在骨子里的烙印。有人问他累不累,他指着胸前的警徽:“你看这警徽,一半是麦穗,一半是盾牌。护住了麦穗里的烟火气,盾牌才有分量。”
如今,甘泉县公安局那个步履匆匆的身影还在,虽然岗位发生了变化,但群众还没有忘记他,他走过的田埂长出了新苗,调解过的家庭添了笑声,守护过的夜晚依旧安宁。郭江浪说,他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,可那些被他温暖过的人都记得,有这样一位当过兵的人民警察,把他们当亲人,为他们办事尽心竭力,是个“好后生”。郭江浪从“橄榄绿”到“警察蓝”,变的是制服的颜色,对事业的忠诚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永不变!(供稿:甘泉县公安局)
责编:刘朋涛
编辑:刘佳怡